《廣島之戀》中意識流動鏡頭的作品分析(圖)
《廣島之戀》這部電影是由回憶和現實構成的,完整地敘述了兩段故事。它把過去記憶拆分拼貼,然后插進按照時間進程發展的現實中。從時間角度上,是把兩個小時的記憶插入40小時的現實生活。插入手法是亂序的,以重復、疊印、相似場景轉移等方式連接過去和現實。片中出現大量獨白,觀眾隨著女主的娓娓道來逐漸了解女主的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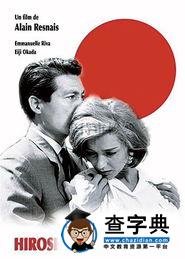
意識流電影有強烈的主觀性,往往是表現主人公的回憶、遺忘、潛意識,記憶與遺忘的矛盾是《廣島之戀》的核心內容,女主在廣島遇到一個情人,他的眼睛他的聲音讓女主回憶起自己的初戀,關于自己的初戀女主回憶地支零破碎。兩個都已成婚的人之間產生了強烈的愛情,兩人分不開,又不能在一起,分開會難過,留下又毫無結果。面對這種必須做出選擇的局面,男主表現地堅定,雖然不知未來如何,但是他是一定要留下她的。女主表現地很動搖,她愛他,他讓她想起自己年輕時,但是過去的記憶太痛苦,她不想再想起過去,不想再來一次奮不顧身的愛情,越是想遺忘越是清楚。所以影片中她表現地很激烈,猛然地轉頭、閉眼、埋頭等動作非常戲劇化,以表示她內心的糾結。猶猶豫豫,反反復復,女主要走,男主追上,再次重分,分分合合,一共四次,重逢在劇場、機場、酒吧和賓館。最終女主留了下來,不過我們可以想象到日后必然還會有離別。
意識流電影傳達了一種不確定性。人物是不確定的,時間和空間也是不確定的,愛情也是不確定的。《廣島之戀》中男主和女主沒有名字,也沒有介紹他們的身份,只是在影片最后男主說:我的名字是廣島,你叫涅威爾。男女主可以是任何人也可能誰都不是,這樣的好處是讓人們關注故事本身,他們是用來闡述導演或編劇想法的工具。時空非常跳躍,一會現實一會回憶,由于《廣島之戀》是黑白片所以記憶和現實的界限不明顯。男女主的愛情是否真實也不可知。女主帶領著觀眾沿著故事主線思考,不確定性可以使思維得以延伸。
藝術結構上,意識流電影徹底地打破了原來的時空觀,將邏輯的,線性的時空觀改變為錯綜復雜的心理時空觀,心理空間在時空轉換中獲得極大自由。《廣島之戀》的混亂不僅表現為在現實中不斷插入回憶片段,還在于它插入的回憶也是凌亂的,并不按照初戀的相識相戀分離順序插入,而是哪一部分記憶給女主造成的創傷強烈就跳出哪一部分。一切都是按照女主的心理時間流轉的,表現過去與現實的沖突。
特立獨行的電影語言也是意識流電影的一大特點。閃切的技巧用于表現意識瞬間流動,比如:女主突然想到的小白樓、倒在血泊里的戀人、小窗戶,一閃而過。很多時候女主站在戀人面前微笑,但是思緒已飄向遠方。十四年中女主以為自己早已遺忘的過去其實一直在她心底。重復技巧的使用也很明顯,小窗戶的影像出現了三次,用于表現無辜的少女因愛情被懲罰,世俗的冷漠,也具象為被關在地窖的少女對外界的渴望。有一段對白首尾都出現了,構成首尾呼應。相似場景轉移是很巧妙的變化場景模式,目的是使得過渡自然。例如: 19:18s男主在床上睡著時手指不自禁地向內蜷曲,女主回想起自己的初戀----德國士兵臨死前手指向內蜷曲;47:40s 女主握緊男主的手,回想起自己在地窖企圖用雙手刨洞逃生,但是鮮血淋漓;55:30s 被剃光頭發的少女被母親擁入懷中,現實中女主也被男主擁入懷中。這些相似場景變化使得影片在過去與現實中來回游走,游刃自如。《美國往事》也是在相似場景轉移方面做得相當優秀的影片。
《廣島之戀》是左岸派的代表之作。左岸派屬于歐洲現代主義電影流派,比新浪潮更加豐富極端。50年代末,大量導演和新小說派作家住在塞納河左岸,其中就有導演阿侖雷乃和女作家杜拉斯,他們分別擔任了《廣島之戀》的導演和編劇。由于作家加入電影創作群體,所以影片更具有文學性,主要表現為影片中大量的獨白和空無一人的外景,用當下的話來說就是很文藝。從影片中我們不難發現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學說,他們深深影響著左岸派的電影創作。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