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18時,首都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中藥藥劑學系系主任王滿元握著手機的那只手有些發顫,他在連續撥打導師屠呦呦的電話。但是,電話始終占線。
作為屠呦呦的關門弟子,也是屠先生一生帶過的唯一一位博士生,王滿元想在第一時間和老師分享這個不期而至的驚天喜訊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剛剛宣布,授予屠呦呦與另外兩名科學家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既是中國科學家因為在中國本土進行的科學研究而首次獲諾貝爾科學獎,也是中國醫學界迄今為止獲得的最高獎項!
直到晚上7時左右,王滿元才撥通電話。電話的那一頭,導師屠呦呦一如往常溫和的聲音中,略顯疲倦。對于獲得諾獎,她言語淡定,這回又要忙了。
實際上,這兩天,屠呦呦家20平方米的客廳里迎來送往,前來道賀的老朋友、老同事,以及從四面八方聞訊趕來的媒體記者們絡繹不絕。
10月6日上午,王滿元和同事到訪時,她正端坐在聚光燈下,操著江浙口音回答記者們的提問,精神不錯,只是一宿未眠,神情中略帶倦色。看到客人中有兩個小孩,屠呦呦中斷了采訪,上前逗了逗孩子,迭聲招呼從冰箱取來糖果分給他們。
慣常,老兩口兒會留一行人吃午飯。為了不打擾導師休息,他們決意回去。走到樓梯口,屠先生看著空蕩的樓道說:幸虧是國慶假期,周圍的鄰居都出去玩了。要不然,要給左鄰右舍添麻煩嘍!
從2000到1的求索
王滿元第一次認識自己的導師屠呦呦,是通過一本筆記本。這本32開深綠色的筆記本,記載著她年輕時對中藥中各大類化學成分提取、分離的一些信息。2002年,王滿元剛剛入學時,屠呦呦將這本筆記交給他,讓他對植物化學有所了解,在當時的王滿元看來,這本寫滿了中藥藥材化學屬性的筆記依舊不過時。
透過泛黃的扉頁,王滿元仿佛看到了一位嚴謹篤行的學術前輩每日伏案的瞬間。這本扉頁上寫著向雷鋒同志學習的筆記,成稿于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初,當時屠呦呦剛剛接手中國抗瘧疾藥物研發的523項目,在科研資料不易得的情況下,很多中藥信息只能從各地學校革委會的傳閱材料中收集。每每獲得,她就抄錄其中,纖毫必錄。用了3個月時間,她收集了包括內服、外用、植物、動物、礦物在內的2000多個方藥,對其中200多種中草藥380多種提取物進行篩查。
從2000到1,她與同事開始了愛迪生般的試錯之路,結果包括青蒿在內的中藥提取物,對瘧原蟲的抑制率都不如傳統的氯喹效果好。難道在中醫藥這個寶庫就掘不出寶來?一個氯喹不可超越,一個常山已到盡頭,真的無路可走?屠呦呦不死心,她又回到原點,從典籍出發,在東晉葛洪所著的《肘后備急方》中找到了鑰匙。
屠呦呦立即改用沸點較低的乙醚進行實驗,終于發現了青蒿素。1971年10月4日,經歷了190多次的失敗之后終于成功,獲得對鼠瘧、猴瘧瘧原蟲100%的抑制率。
1981年,在北京召開的青蒿素國際會議上,青蒿素在世界舞臺上嶄露頭角。會議主席世界衛生組織瘧疾化療科學工作組阿南德教授高興地說:青蒿素的獨特結構和抗瘧作用方式,是和任何已知的抗瘧藥毫無雷同之處,這就為今后設計合成新抗瘧藥提供了新思路。
青蒿素的最終命運果真被阿南德言中。這株小草和其蘊含的神奇化學式,成為拯救千萬瘧疾病人于水火的救命藥,也使得屠呦呦和青蒿素的發現成為中醫學校課堂上的經典一課。
在肯尼亞的瘧疾重災區奇蘇姆省,青蒿素藥物科泰新治愈的一名瘧疾孕婦,將生下的孩子取名科泰新。有評論認為,青蒿素的發明,其人道主義價值要高于青霉素。這或許是屠呦呦獲獎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在屠呦呦獲獎前,另一位華人諾獎得主楊振寧先生很早就相信青蒿素能摘得諾獎桂冠。2011年9月,屠呦呦就已獲得被譽為諾貝爾獎風向標的拉斯克獎。她也因此成為諾獎的重要人選。此后,每年諾獎公布前,他的學生都會守在電視機前,等待獎項的揭曉。這些年的期望一次次落空,幾乎讓人覺得青蒿素已經獲獎無望。在2015年湯森路透的諾獎預測名單中,屠呦呦也名落孫山。
這是一個國際學術界遲到了39年的認可!事實上,早在1972年11月,屠呦呦課題組就獲得了抗瘧有效組分青蒿素單體化合物。這次獲獎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學界多位專家如此評價。
至于公眾關心的年事已高的屠呦呦能否出席頒獎儀式,目前仍不明朗。她的血相指標一直都不太好,或許是當年提取青蒿素,接觸大量乙醚,導致中毒性肝炎,屠呦呦的身體一直不太好。2011年那次去美國領取拉斯克獎回來,長途顛簸,又加上年過古稀的她老年病較多,回來后她的骨頭疼了一年。王滿元說:前幾天她獲得哈佛大學醫學院授予的華倫阿爾伯特獎時,也因身體原因未能成行。
輿論旋渦中的中國神藥
屠老師獲獎后,朋友們問我是什么感覺,我說是復雜,并不完全是激動和興奮。讓王滿元掛心的是,在持續發酵的諾獎熱度中,因為屠呦呦的中醫藥研究背景引發的獎項是授予傳統醫學還是現代醫學的爭論,讓這個國人首次的獎項面臨的語境愈陷復雜。
屠呦呦所獲得的這個諾貝爾獎,究竟是授予傳統醫學,還是現代醫學?一時間,國內輿論莫衷一是。有人認為,屠呦呦的獲獎代表了中醫的勝利,甚至有輿論將青蒿素冠以中國神藥之名。
在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公布后的新聞發布會上,諾貝爾獎委員會成員、發言人漢斯弗斯伯格表示:我們不是把本屆諾獎頒給了傳統醫學,我們是把獎項頒給被傳統醫學啟發而創造出新藥的研究者,可以說,這是受到了傳統醫學的啟發,但這個獎項并不是給傳統醫學的。
中國中醫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曾任中藥所藥理研究室主任廖福龍對此回應,屠呦呦的獲獎在日后會逐漸顯現其重要意義,它將鼓勵研究者更多地將目光投向傳統醫學寶庫。國際學界對中醫藥的認識是比較膚淺的,青蒿是中國幾千年來使用的草藥,從中提取出有效成分,這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說明中醫藥這種臨床實踐和過去的文獻積累,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指出,中藥里大部分復方藥還有廣闊的空間,對其研究實際上代表了中藥研究不同于青蒿素提取的另一條道路。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原院長饒毅等人曾在《中藥的科學研究豐碑》一文中指出,青蒿素的發現證明了一條成功的中藥研究的道路,即確定中藥特定化學成分和特定疾病的關系,用傳統的藥物尋找全新化學結構的藥物、發現已有化合物的新用途。他表示,這種模式打破了對中藥必須使用復方,且不能按照現代科學標準來評判,必須用它自己特殊的標準的成見。
在對中醫或褒或貶的爭論中,這兩種來自學界的代表聲音各有擁躉。有聲音指出,正是中國醫藥界尊復方藥研究為主的現實,讓屠呦呦多次與院士評選失之交臂。
老祖宗留給我們很有價值的寶庫,里面有很多東西值得深入挖掘,但是如何利用幾千年前的東西,應該是當代科技水平的體現。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張伯禮認為,將傳統醫學的思維、經驗與現代科學技術巧妙結合,有助于原創性醫學成果的產生。
屠老師并不關注她的研究在中醫中藥領域的歸屬問題,也不關注對中醫是不是科學的爭論,她在心里堅信,傳統醫藥是個寶庫,而現代科技可以提高中藥療效。王滿元眼中的屠呦呦,是一位在科研生涯中將中藥現代化作為畢生追求的醫藥科學工作者。
呦呦求蒿,其心也癡
青蒿素,是中國神藥!
每次聽到別人這么說,屠呦呦都會搖頭。在她看來,青蒿素不能包治百病,但應該物盡其用,而我們對它的認識可能還只是管窺一豹。
青蒿素這個星星之火,雖然一直在燒,卻并沒有形成燎原之勢。在中藥所里,盡管屠呦呦如同一個傳說,但真正在做青蒿素研究的人并不多,還是按任務定規模。被外界熟知的青蒿素研究中心也只是中藥所大樓9層的兩間實驗室和一間辦公室。
2002年,屠先生承接的中藥標準及相關中醫藥臨床療效評價標準專項中有關青蒿的子項目,當時唯一的組員楊嵐研究員將要去日本進修。因為人手缺乏,當時剛剛考取了屠呦呦博士生的王滿元,就被要求提前進組。彼時72歲的屠先生每個月都會打車到實驗室,指導王滿元開展相關研究。
1992年,雙氫青蒿素被批準為一類新藥后,屠先生就將研究的重點轉向了青蒿素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療上。研究中,屠先生發現,青蒿素對紅斑狼瘡的治療效果明顯。直到2004年,雙氫青蒿素片獲得藥物臨床研究批件。
但是,這份批件一直塵封在屠先生的辦公桌里。一個現實的困境讓她無法開展臨床試驗錢。
當時,沒有藥廠愿意提供經費,因為雙氫青蒿素對紅斑狼瘡治療只是增加了藥物的適應癥,藥物的制備工藝改變不大,對企業來說,利潤難以保證。王滿元說。
此后,屠先生多方聯系相關藥廠,積極爭取科研立項,希望能申請到科研經費,填補臨床試驗的巨大投入缺口,但始終無果。直到拉斯克獎頒獎,這份臨床研究批件才被重新得到關注。然而,此時這份落灰批件已經過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屠先生的名字來自《詩經》名句。宋代朱熹曾注稱,蒿即青蒿。這根堅韌的野草成就了她一生在科學曠野中求索的宿命。呦呦求蒿,其心也癡。
屠老師究竟算西醫還是中醫呢?
每次有人這么問她,屠先生都微微一笑,不作回答。王滿元說,中醫西醫之爭,屠呦呦并不關心。
屠老師一輩子做科研的奔頭兒就是利用科學技術探索中藥更好的療效,她對我的培養也是堅持這個信念。王滿元一入學就收到老師的禮物屠呦呦已畢業的碩士研究生吳崇明和顧玉誠的碩士論文。這兩篇研究傳統中藥延胡索、牡蒿、大薊、小薊的有效成分或化學成分的論文,承襲了屠呦呦做青蒿素研究的方法。王滿元認為,這份禮物不僅意在讓他揣摩其中的研究思路,也是對師門傳統的一次研習。
在他攻讀博士期間,屠先生還出資讓他去北大醫學部、協和醫科大學學習中草藥化學、波譜解析等課程。
屠老師是一個特別執著、堅定、事業心特別重的人,心無旁騖。王滿元告訴中國教育報記者,屠先生平時有做剪報的習慣,尤其關注健康衛生領域的重大事件和新聞,經常讓王滿元尋找相關資料補充知識。在非典期間,她和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合作,研究青蒿素類藥物對非典疫情可能的治療效果。
他們這一輩科學家,有著很強的國家榮譽感和集體歸屬感,也有著很堅定和樸素的科學信仰。她對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從她身上,我學到了做科研,在找到你關注的方向后,就要堅定地走完科研道路。王滿元說。
中醫科學院主樓廣場一側的墻上,寫著1958年毛主席對中國衛生行業的期望: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這也是屠先生一生的寫照。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推進雙一流 廣西大學強力“脫水”2018-12-10
推進雙一流 廣西大學強力“脫水”2018-12-10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工程教育2018-09-30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工程教育2018-09-30 讓馬克思主義真理之光照亮未來2018-05-07
讓馬克思主義真理之光照亮未來2018-05-0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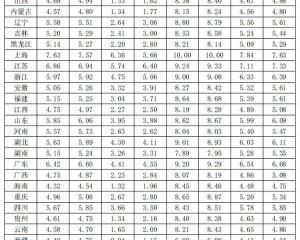 《中國教育指數2017》正式發布 12個維度數繪教育圖景2018-03-05
《中國教育指數2017》正式發布 12個維度數繪教育圖景2018-03-0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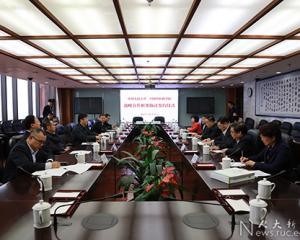 中國人民大學與中國中醫科學院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2018-01-27
中國人民大學與中國中醫科學院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2018-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