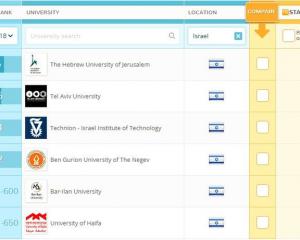教育部原副部長章新勝專訪二
【文章原載于教育部《世界教育信息》雜志2010年第2期,作者:周一、熊建輝】
荷花、綠葉與水土:
——教育部原副部長章新勝談高等教育國際與本土化
文/周一 熊建輝
國際教育是面向世界的教育
記 者:您曾在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哈佛大學等一流高校求學,在擔任教育部副部長期間又長期分管國際教育、政策法規、教育研究等工作,有著極為廣闊的國際視野和豐富的國際教育管理經驗。首先請您談一談對國際教育的看法。
章新勝:什么叫國際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其實,它涉及的面特別廣,目前學術界對這個概念還沒有形成統一、明確的界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提出,國際教育是對促進國際理解、合作與和平教育的一種簡要表述。《國際教育百科全書》主編胡森認為,國際教育作為一個學術領域,指對教育領域國際問題和跨文化問題的跨學科研究;作為一個實踐領域,它涵蓋了旨在促進國際理解的所有教育努力,如學習和掌握外語,增進對其他國家、地區和民族文化知識的了解等,以及實施這些教育活動的機構和制度,如與之相關的機構、項目、正規教育或非正規教育的課程等。弗里曼·巴茨(Freeman Butts)在《教育百科全書》中也指出,國際教育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本國學校觀念與課程的國際化,或稱為“世界事務教育”,旨在影響各級學生的知識、價值觀和態度;二是某一個國家師生到其他國家教育機構學習或研究,即師生的國際流動或跨國教育交流;三是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改進其衛生、經濟、教育機會和民眾福利的教育援助。
歸納起來,國際教育可以是師生的國際流動,如來華和出國留學、海外游學和訪學等;可以是師資隊伍(包括管理隊伍)的國際化;可以是教學與課程的國際化,如外語教育、國際理解、跨文化交流、世界歷史和地理等方面的課程;可以是國際聯合科研;可以是國際合作辦學;可以是不同國家之間的學歷和學分互認;也可以是一個國家的對外教育政策;還可以與比較教育結合在一起作為單獨的一門學科、一種研究方向,等等。以上都屬于國際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僅從某一個方面去理解就可能會失之偏頗。國際教育的核心是瞅準全球趨勢,追蹤世界前沿,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認可的理念行事,培養出能真正面向世界、具有區域和全球視野以及國際理解和跨文化交往能力的復合型人才。簡而言之,國際教育就是一種面向世界的教育,一種開放的教育。
中國近代高校頗有國際眼光
記 者:從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來看,您認為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情況如何?
章新勝: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時的有識之士認識到,要富強就要辦學,要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做到“師夷長技”。中國近代的高等教育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下產生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浙江大學、東吳大等近代意義上的大學紛紛成立。除了由政府辦大學,這一時期西方傳教士紛至沓來,辦了一些教會大學,如圣約翰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中國一些知名民族企業家、教育家也很有精神,舉辦了不錯的大學,如南開大學;還有一些大學,如滬江大學,不管其水平如何,都反映了中國近代智士仁人的教育救國的理念。當時,很多學校的創辦者都很有智識,不少學校都在倡導教育救國,辦學也都相當國際化。
以八年抗戰期間的西南聯大為例。西南聯大十分強調課程設置,即先明確受教育者應該學到什么,然后根據這一理念來設置自己的課程體系。我看了西南聯大的本科生課程體系之后,對其背后所蘊藏的教育理念十分感嘆,難怪其畢業生中會出現像楊振寧、李振道這樣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趙九章、鄧稼先等“兩彈一星”功勛獎獲得者,黃昆、劉東生、葉篤正等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宋平、彭佩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難怪它在當時被稱為亞洲最好的大學。它的課程體系和我在哈佛大學讀書時的課程體系有相似之處,都強調以人為本的全人發展。
據說哈佛大學的創辦人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所以哈佛最開始效仿的是劍橋大學的體系(如強調以人為本的學院制),然后又學習洪堡大學的做法,最后開創出自己獨特的體系。我們現在只重視這些大學的科研體系,而很少注意它們獨特的人才培養模式。西方大學育人模式的核心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有人將之翻譯成“通識教育”、“博雅教育”或“博識教育”,但這些譯法都不盡如人意,只強調了“博”,沒有強調英文原文所包含的“Tolerance”,也就是“兼容并包的”、“匯通百家的”意思。其實,“Liberal Arts Education”有“寬容的、自由的”,“思想解放的、以人為本的”,“注重多樣化的、注重因材施教的”等含義,這種教育是學生在導師指導下,自己主動建構適合自己的課程體系的過程,是拓展人心智的教育,它特別注重學術自由,以學生興趣為導向,培養學生好奇心和批判精神,使學生逐步做到觸類旁通。例如,在學生本科階段,洪堡大學并沒有一開始就注重學生技術和職業能力的培養,而是首先提倡“Liberal Arts Education”,其核心是把一個人當成完整的人來培養和塑造,也就是“全人培養”、“全人發展”,英文稱為“Holistic Development”或“As A Whole Person”。這種教育理念同樣也體現在西南聯大的課程體系中。
所以,我覺得,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培養出這么多的大家和各個領域的杰出人才,與它的人才培養模式、國際視野以及結合中國深厚傳統積淀引進先進課程體系的做法分不開。更重要的是,它結合了當時中國的國情,通過抗日、愛國這樣的國情教育來激發人的心智的鍛煉,首先拓展學生的心志,使其做到文理兼修;然后開展“Liberal Arts Education”,也就是兼容并包、融會貫通的教育;最后,才提倡創新,培養學生成為有道德、有知識、有能力、有抱負、有紀律的人,為國家作貢獻。所以,西南聯大的教育是真正的德、智、體相結合的全人教育的典范,也只有這種教育才能真正培養愛國家、有激情、有熱血、有創造力的人才。可以說,西南聯大是中國人有能力辦成與歐美一流大學相媲美大學的成功實踐。
中國高校需要面向世界辦學
記 者:正如您前面談到的,中國近代高校辦學很有國際眼光。那么,您如何看待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面向世界這一問題?
章新勝: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高等院校經歷了比較大的變革。第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進行的院系大調整。雖然我們當時打破了不少大學原有的綜合性體系,但那是為了配合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也部分受到了前蘇聯戰時經濟等特殊情況以及前蘇聯援助的156個大項目建設等的影響,離不開當時的國際背景,是當時我們這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戰略。雖然這種做法使大學本科知識有所分離,但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這種做法對我國建立相對完整的工業及經濟體系、完成相對獨立的教科文衛體體系的初步布局是有積極作用的。當時由于西方的封鎖,我們與西方交流的大門被迫關閉,新中國的教育與前蘇聯、東歐的教育交流與合作比較多,學生大部分被派往前蘇聯和東歐。1950年~1965年,我們共向前蘇聯、東歐、朝鮮等20幾個國家派出了10 698人,其中派往前蘇聯8 320人,約占派遣留學生總數的78%;同時,出于培養翻譯人才的需要,我國還向極個別西方國家派出了少量人員學習語言。當然,這一時期還有一部分從西方回來的留學生,為教育的國際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次大變革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到世紀之交。這次全國性院系調整熱潮按照“共建、調整、合并、合作”的八字方針進行,改變了我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部門和地方條塊分割、重復辦學的局面,基本形成中央和省級人民政府兩級管理、以省級政府管理為主、提倡公辦民辦高校共同發展的新體制,建立了一批多學科、綜合性、研究型的大學,為我國的科研和高技術領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我們培養一大批國際化、復合型人才,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智力支撐等奠定了基礎。
我們可以發現,上世紀50年代院系調整時期,我國高校發展呈現區域國際化特征,還不能稱為全球化教育;而我國高校現在正在實施的國際化戰略,其實已經離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教育不遠了。
1983年,小平同志應北京景山學校之請作了“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題詞。這句話雖然只有短短的16個字,但所蘊涵的思想卻極其豐富。小平同志提出的是“三個面向”,而不是“兩個面向”,教育不只要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還要面向世界。這在當時非常有遠見!那么,他所說的面向世界指的是什么呢?我認為,絕對不是建國初期那樣只面向前蘇聯和東歐,也不是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那樣主要派遣留學生到北美、歐洲、日本,而是面向整個世界。當然,除了派遣留學生出國,我們在教育交流與合作,包括聯合科研、師資培養以及來華留學生教育等方面,都需要面向世界。
在全球化的今天,知識、人才、科學技術、學術研究的流動都是全球化的,這是世界潮流。高校無論是從事科學研究,還是進行人才培養,如果不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考慮,怎么能夠創建出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學和一大批國際化大學呢?怎么能培養出一批世界一流的人才和一大批國際化人才呢?怎么能產生世界一流的成果呢?所以,我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非常重要。它不僅僅是大學的一個方面,而是滲透和服務于教學、科研、校園文化、人才培養、校園規劃與建設等各個領域。在21世紀的今天,不談教育的國際化而閉門造車,恐怕沒有哪個國家愿意這樣做!關起門來是不行的!!
我們現在的大學,包括高職院校在內,都在制定學校發展的戰略規劃。我認為高校的規劃確實應該放在國家戰略的高度和全球的視野中來看。為什么呢?很簡單,這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高校的發展與國際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高校必須緊緊抓住機遇,服務經濟和社會發展大局。我國GDP中貿易進出口的比重已經由20%上升到40%。事實上,全球化已經本土化了,也就是“Glocalization”(由“Globalization”和“Localization”兩個單詞演化而來,有人將之翻譯成“全球本土化“、“球土化”等)。世界上沒有哪個跨國公司、沒有哪個知名的服務性企業不在中國設立機構或者生產產品。全球本土化在經濟和產業界有很多非常典型的例子。同樣,正如美國、歐洲的文化產品,甚至“韓流”都在中國找到了生長的土壤,我們的文化產品也開始走向世界。此外,現在很多本土性和區域性的問題也已經全球化了,如甲型H1N1流感、艾滋病等流行病,以及能源、糧食、氣候、環境、反恐等問題。所以,不論是自然學科、社會學科,還是人文領域、藝術領域,國際交流都體現出了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雙重特色。
在1997年的亞太金融危機中,中國被一下子推到亞洲的中心,在2009年的全球氣侯大會中,中國一下子又被推到世界的中心。在這種背景下,高校發展也需要考慮面向世界,在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師資隊伍建設、來華留學生培養、校園規劃等各個方面,面向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教育是服務于經濟社會、服務于國家發展、服務于國家戰略、服務于大外交的;教育不能只是緊隨其后,而更應先行一步,具有前瞻性。教育能夠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城市的未來,今天的情況是昨天教育的結果;今天教什么將成為明天的結果,而明天的中國將更加國際化、全球化。
科研成果和技術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過程中,哪里有其發展的最好土壤,它們就在哪里安家落戶。比如,3G手機實驗室原來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現在設在中國。為什么它要設在中國?因為中國有7億手機用戶,約有1億中國用戶在用手機上網,而各種媒體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將來手機將成為一個集成各種信息資訊的終端,中國的市場也將隨之變得越來越大。另外,中國人聰明勤奮,勞動力成本相對一些西方國家也比較低,所以,這個實驗室設在中國是最佳選擇。不僅科研在呈現全球化,教科文衛體等領域也在日益全球化,各行各業都需要人才,因而人才的培養也要全球化。中國的產品已經走向世界,而我們的人才能不能走向世界?我們的人才怎么走向拉美?怎么走向非洲?怎么走向阿拉伯?怎么走向東亞、東南亞、南亞和中亞?……這個課題已經擺在了我們面前,教育面向世界的問題確實很迫切。
高等教育大眾化之后要走多樣化發展之路
記 者:確實,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的高等教育面向世界已經是一個刻不容緩的課題。那么,您認為中國高等院校應該怎樣面向世界?高校在國際化進程中應該重點關注哪些問題?
章新勝:第一,這要看我們現在的大學在領導體制、組織制度、機構設置、管理模式、人才培養及教學模式、國際化視野等方面與國際上優秀高校的差距,然后努力縮小差距。這不只是引進幾本原版教材、招募幾位能用外語開課的教師、開設幾門雙語課程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教學方法的問題。當然,教學方法是很重要的方面,比如要倡導互動、探究的教學方法。
第二,我們的人才培養模式有很多自己的特點,但是在全人發展和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培養學習興趣等方面,還大有潛力可挖。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學校、家庭等各方面實際上更加重視智育,對體育、德育的重視程度并不夠。當然,黨和國家非常重視德育工作,教育部門也非常強調德育工作,但是在家庭中實際上很難做到,現行的應試教育就是一個很大障礙。所以,在如何重視全人發展,重視德智體全面發展,如何培養學生走向社會、關愛社會等方面,我們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還需要做很多工作。
第三,我們不僅要關注“教”和“育”,不僅要重視知識傳播,更要重視全人發展,重視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我們現在過于強調專業界限,把專業分得太細,不僅是“切塊”,而且是“切絲”,而很多專業從學科角度來說其實是一個整體。不少發達國家的大學一、二年級不分專業,三年級才分專業;它們不僅重視技術和職業技能的培養,以及一個人成為國家合格公民、世界合格公民的培養,更重視全人發展、創新能力的培養。這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第四,評估體系需要與國際接軌。國外大學的評估體系很重視同行評估,很重視社會各界人士、第三方及國際人士參與評估。我覺得這非常重要。恐怕難以將“自己來評估自己”的評估體系下的大學稱為國際性大學。
第五,在高等院校的整體辦學制度上要明確公辦、民辦共同發展的格局。我國高校在世紀之交已進入大眾化階段。如何保證公辦、民辦高校,包括優質資源的中外合作辦學,形成一個共同發展、相互競爭、互為補充的格局,做到大眾化與多樣性相結合,是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以后不得不思考的一個問題。美國高校在20世紀50年代末進入大眾化階段,大學發展出各種類型,有教學型大學、研究型大學、應用型大學,有公立大學、私立大學,還有綜合型大學和只從事本科教學的學院,在后者中有些教學質量與哈佛、耶魯不相上下,甚至還要高一些,如阿姆赫斯特學院、威廉姆斯學院等。此外,美國還有一大批以培養應用型技術人才為主要任務的社區學院。中國現在的學校,很多都是專要升本、本要升綜合、綜合要升研究型、師范要轉綜合。這種縱向性提升、行政性驅動下的高校架構容易導致“千校一面”,無法實現多樣化發展。我真心希望我們的學校在多樣化發展進程中,每一種類型的學校都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都有排頭兵,而不是只建設一批世界一流或知名的高水平、綜合性、研究型大學。
第六,師資來源國際化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現在來華留學生越來越多,我們的學校需要廣開渠道,吸引更多在世界各國教書的留學人員回來,吸引外國退休的教師來華。如果一所學校的教師以本國甚至本省市、本學校畢業生居多,那么它很難成為一所國際性大學。我們如何能騰出一些位置,吸引那些有教學經驗的、在國外擔任教師的人才回來,吸引那些在國外跨國公司、商業銀行、保險公司、政府及其他社會部門有實踐經驗的人才來做兼職教授,我覺得這是高校國際化發展進程中十分關鍵的一環。如果海外名校的教師能主動來我們的學校做訪問學者、訪問教授或研究員,并將之作為其職業生涯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世界主流大學的學生愿意自費來我國高校攻讀學位,那么,我們的學校就會成為國際化的高水平大學。
第七,生源國際化也很重要。現在我們面臨著極大的機遇,有兩個數字就很可喜:一是留學回國人數的增幅高于出國留學人數的增幅;二是來華留學人員的增幅高于出國留學人員的增幅。我國大學,尤其是一些邊境省份的大學招收了大量周邊國家的留學生,此外還有部分優秀來華留學生進入北大、清華、復旦、浙大、南大、南開等國內知名大學就讀。現在,來華留學生已超過20萬,但我認為我們還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生源國際化對人才培養國際化有重要意義。在一個大學課堂里,如果本科生中能有3%~5%的國際學生,研究生中能有15%~20%,甚至更高比例的國際學生,人才互動的作用才能凸顯出來。來自不同社會、文化、歷史、地理背景的學生,其視野和思維方式是很不一樣的,讓他們在一個大的教育環境中互相交流、溝通、合作,在不同文化的沖突與融合過程中完成學習活動,就有可能培養出國際化人才。而要吸引國際一流學生,需要多方面的條件。比如,招考制度要公平、科學,選拔制度要綜合考慮一流學生的實際情況;還有財政制度,這涉及校友會的建設,如校友的捐款制度,等等。美國在獎學金、科研經費等方面的競爭性制度,為吸引世界一流人才、實施世界一流教育、開展世界一流科研打開了大門,很值得我們借鑒。合理的招生制度、有吸引力的獎學金制度等是保證國際優秀生源的重要條件。此外,在吸引國際一流學生前來就學以后,我們能否開設好的雙語課程,也是保證生源國際化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我們現在有多少學校能用英文(且不說用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等)開設完整的課程?我們的大學在發揮社會主義優勢方面還有很大的潛能可挖,在根據比較優勢進行統籌規劃方面還不夠,課程往日還太少且比較分散,不利于整體優勢的發揮。當然,我們現在發展的步伐很快,形勢很可喜,但確實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
第八,高校要更好地面向世界,還需要在學分制、必修和選修課程等方面進行改革。學分制涉及學校整個體系的改革,正如窺一斑可以知全貌。我們現在的大學基本上還是實行百分制,還沒有實施完全意義上的學分制,如平均成績點數(GPA,Grade Point Average)。實施真正意義上的學分制有利于創新人才的培養和全人發展,對我們現在強調的創新精神培養和品德養成具有積極的意義。在選修課程方面,即便是我國的頂尖大學,這一比重還是較低,大多數學校才占20%左右,而哈佛、耶魯、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學的選修課程比重都已超過40%。當然,這涉及人事制度、教師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變革。雖然我們與世界一流大學差距不小,但我們蘊藏著未來發展的無限潛能。如果說一百多年前的世界一流大學主要分布在德國等歐洲國家,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一流大學主要分布在美國,那么,我堅信,在本世紀中葉實現“三步走”目標中的第三步,即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時候,我國的大學將在世界一流大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創建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體系任重道遠
記 者:據不完全統計,近代以來我國翻譯的國外著作有10多萬冊,但西方翻譯中國的書籍只有1 000冊左右。2003年,近80高齡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在其著作《治國方略———應對變化中的世界》(Statecraft: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中,談到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她說中國不會構成冷戰時期前蘇聯的那種挑戰,中國不可能成為超級大國。她解釋道,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而削弱西方國家的具有國際感染力的理論,今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甚至不是電視節目)。結合教育,有人認為,今天談論教育改革的人,缺少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尊重。您如何看待我國教育改革中的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
章新勝: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我曾多次引用英國前首相撒切爾的這段話來激勵我自己的思考,也與我們的大學校長進行探討。她說不要擔心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因為她沒有產生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理論和思想。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所走的道路就是始終堅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所開創出來的一條現代化的新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國家所提出的生態文明理念就可以引領世界潮流,它是對西方工業文明的反思,比起西方提出的氣候變暖問題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人類在經歷了近300萬年的原始文明、3 000年的農耕和游牧文明、300年的工業文明之后,到現在已經難以為繼,生態文明將是世界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又如,我們所提出的共建和諧世界的理論,無疑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是能夠起到引領世界潮流作用的。當然,不管是建設生態文明,還是共建和諧世界,中國模式的現代化道路給我們的高校提供了無限發展的空間和生產普世理論的歷史性機遇。
確實,我國當前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前列,但我們在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在知識和理論創新等方面、在產生有國際影響力的思想方面,還遠遠不能和我國的經濟地位相匹配。以國際公認的產生理論和思想的三大引文索引為例:從SCI、EI引文索引的數據看,我們在總量上雖然已經躍居世界前列,但影響因子卻很低,這說明我們的科學研究的原創性還很不夠;在SSCI方面,盡管我們研究成果的總數在增長,但卻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這說明我們在提出理論、產生思想,特別是有國際影響力的理論和思想方面處于起步階段,而且在被世界所接受和認同方面還有較大距離。當然,這同時也說明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因此,要確保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我們就必須不斷創新,在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在知識和理論創新等方面加倍努力,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強大支撐。
在歷史上,中國產生過很多有國際影響力的思想,比如“天人合一”、“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和而不同”、“治大國若烹小鮮”等思想。但我們也必須看到,近代以來中國在這方面落后了。其實,早在上個世紀,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英國人李約瑟就曾問:“為什么近代自然科學只能起源于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李約瑟之謎”,它提出了這樣一個悖論:“為什么古代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端于中國?而哥倫布、麥哲倫正是依靠指南針發現了世界,用火藥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用造紙術和印刷術傳播了歐洲文明。”去年先后辭世的季羨林、任繼愈、錢學森等國內學界大師對此也曾充滿憂慮。例如,錢學森就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學森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事實上,我們現在更多是在詮釋西方的理論,在努力爭取擴大西方架構下的話語權,而在創新和創造方面還做得很不足。我們能不能在學習西方的基礎上,發現和提出具有趨勢性、前瞻性、對世界有指導意義的問題,能不能最終產生對世界有影響、有普世價值、并被世界所接受和認可的思想,是我們的大學和有關研究機構不得不面對的巨大挑戰。
事實上,我一直在思考張伯苓、蔡元培、竺可楨等先生主張的教育中國化問題。他們努力走中國化道路,既學習西方,又努力做到中西合壁,始終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我認為光有“本土情懷”還不夠,而應該是“全球化視野,中國化道路”。德國在總結英法經驗的基礎上走了德國化的道路,美國在吸取歐洲及世界經驗的基礎上走了美國化的道路。中國也要學習世界上先進國家和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應該而且也只能走中國化的道路。國外的教育離不開所在國家的社會制度、宗教、文化、歷史、地理背景等。全球化視野中的中國教育就好比“荷花”,離不開我們的政治體制、經濟社會發展等“荷葉”的扶持,更離不開我們的文化傳統這一“藕根”以及歷史和地理背景等水土的滋養。人們往往只重視荷花,卻忽視荷葉,更無視藕根及其周圍的水土。但其實,荷花雖好,還需要綠葉扶持,更需要水土的滋養。
德國的教育既是國際化的,又是德國化的;美國的教育既是國際化的,又是美國化的。俄羅斯、日本的教育也是如此。它們都是既有國際化視野,又有自己相對獨立、完整的教育體系。以具體的大學為例,哈佛大學就是在學習其他大學先進經驗的基礎上開創了自己的發展道路。正如前面談到的,哈佛曾向歐洲多所大學學習,早在1879年就提出了“Liberal Arts Education”。此后,哈佛大學一直緊跟時代步伐,不斷調整自己的課程體系。最近,哈佛又對它的本科課程體系進行了修改,明確了21世紀要培養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人能稱之為受過教育,他們應該掌握哪些知識和能力、具備什么樣的情懷、視野和精神狀態,等等,并根據這些理念來指導其課程設置。它把國際化和本土化很好地結合起來,所以能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我一向反對經濟和產業界提與國際一體化,更何況是教育。照搬國外先進經驗是不行的,全盤移植只會導致南橘北枳。我們需要對國外的東西進行再過濾,建立自己的標準。本土化就是要消除水土不服的現象。中國的教育自有很深的根基,我國古代的書院、國子監和府學,以及近現代的大學,有不少辦得很好,甚至產生過世界性的影響。我們的教育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根系發達,而且一直從未中斷過。我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走中國化的道路。我們的高等院校要有國際化視野,但更要走中國化的高等教育發展道路。
【文章原載于教育部《世界教育信息》雜志2010年第2期,作者: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周一、熊建輝】
.gif)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