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已經過去整整40年,每當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中國科學院院士、物理所研究員趙忠賢回憶起那次帶來“科學春天”的大會,身為親歷者的他仍異常感慨:“那次大會帶來大環境的穩定,是我幾十年堅持研究的必要保障,我正是依靠了這樣的環境得以發展和有所成功。”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至今正好40周年。3月22日上午,在中國科學院紀念全國科學大會40周年座談會上,趙忠賢和同為全國科學大會親歷者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數學院研究員楊樂以及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等一同回顧紀念了“科學的春天”。
“臭老九”帽子被摘掉
趙忠賢至今記得,在全國科學大會的開幕式上,鄧小平同志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了“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著名論斷。
至此,知識分子“臭老九”的身份正式結束了。
當時只有37歲的趙忠賢就坐在這個會場里。很快他就意識到,這次大會不僅是對科技界的撥亂反正,也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聲,是國家發展、特別是我國科技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他感慨:“政治上的翻身才能感受到春天的氣息。”
趙忠賢回憶,文革十年大多數科學研究停止了,甚至有些國外書籍和雜志都停止訂閱,很多人失去了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會,“對從事科技研究的愿望達到了饑渴的程度,對春天的氣息更敏感”。
全國科學大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在這次大會前后,一系列的重大舉措出臺撥亂反正,比如恢復高考和研究生考試、恢復職稱、恢復學術交流活動等。
趙忠賢記得,在著名的1977年科教座談會上,鄧小平講到,要做科學教育的后勤部長,“這更是說到了大家的心坎里,點燃了大家的心”。
從那以后,各單位著力解決人才問題和發揚學術民主問題,趙忠賢所在的研究所史無前例地成立了學術委員會,按需要建立新的研究室。
他還記得一個細節,當時的中科院考慮有些年輕人十幾年沒漲工資,生活太困難,就采取了補貼的措施,每月發10元、15元、20元三種津貼,那時一名大學畢業生每月工資大約56元。
巨大的歷史潮流中,一些個人和單位的命運也隨之改變。
楊樂學術職稱的恢復就是如此。
1977年10月,中國科學院在中央的批準下,將陳景潤從助理研究員破格提升為研究員,提升楊樂和張廣厚為副研究員,過了不久,又將后兩位提升為研究員。這3位后來成為人們所熟知的大數學家。
科技春風吹向大江南北
第二年,也就是全國科學大會的那一年,科技人員可以出國了。
楊樂清晰地記得,那是1978年4月,他和張廣厚遠渡重洋到瑞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并順訪英國。這是文革以來,我國科技工作者第一次以個人身份出國參加學術活動。
這在當時引起了巨大轟動。
楊樂說,當時為他和張廣厚的出訪,中科院專門給中央寫了申請報告。后來他才知道,在當時的答復文件上,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都畫了圈。
“需要每一位政治局委員都畫圈,這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這個突破對我國科技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楊樂說。
1978年的冬天,開始有成批的科技人員出去做訪問學者。此后,我國科學家參與的國際交流逐漸多了起來。
放眼整個中國歷史進程,如今看起來很正常的科技活動,都是當年一點點地從禁錮中突破而來。
40年前,有一名小學生叫徐濤,他并不記得當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但也感受到了這股從北京吹向大江南北的科技春風,特別是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激發了無數人的科學熱情——孩子們在被問到“長大后做什么時”,都響亮地回答“要當科學家!”
當時,改革開放的政策深度影響著科學界,中外學者的交流已經非常頻繁。1994年,德國馬普生物物理化學研究所的Erwin Neher教授——1991年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得主,受邀訪問徐濤當時所在的研究組,他抓住機會,向Erwin Neher請教問題。
多次深度的交流中,徐濤得到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的青睞,并受邀到德國馬普所跟隨他從事細胞內蛋白質和膜轉運的分子機制研究。1999年,他又來到美國華盛頓大學生理與生物物理系,師從美國科學院院士Bertil Hille教授。
如今,徐濤這位自稱“科學春天”的受益者,已是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大學副校長。
“這40年,是國家改革開放的40年,是科學迅速發展的40年,也是我個人成長的40年。”徐濤說,受益于改革的春風,讓他有機會到世界最頂尖的研究機構學習和工作,這段經歷使他系統地掌握了多學科知識,成為一位擅長多學科交叉的科學工作者,奠定了成就科技夢想的基礎。
改革創新迎接下一個“科學春天”
中科院化學所研究員羅三中是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同齡人。用他自己的話說,也是經濟社會飛速發展、國家日益強大的直接見證者和受益人,同時也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親歷了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的突飛猛進。
在今天的座談會上,他說,他和很多青年同仁一起交流,也形成了強烈的共識和共鳴,即中國處于科學技術發展的最好時期,中國現在已經成為做科學研究最好的地方,同時中國也是對科技創新需求最為緊迫的國家。
正如中科院院長、中科院院士白春禮所說,量子通信、中微子、鐵基超導、外爾費米子、干細胞和再生醫學等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重要科技成果水平達到世界前列,載人航天、空間科學、深海深地探測、超級計算、人工智能等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的戰略高技術領域持續取得重大突破……我國科技創新事業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建成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
中科院院士、遺傳發育所研究員曹曉風也有類似感受,她說,“如今,國家的發展、民族的復興,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先進科技的支撐,新的時代迎接新的‘科學春天’”。
在她看來,新的時代要求科技工作者提升科技自信,勇于攻堅克難,把攻克具有國家重大需求的前沿科學和顛覆性技術難題作為自己的使命,例如工業領域的發動機、信息領域的CPU和人工智能、生物領域的基因編輯等重大創新。
她還建議改善科研管理評價機制。“最好的科研評價,還是允許失敗。”她說,對勇于創新或前沿突破性研究的失敗應采取更寬容的態度,并在一定時期內,給予年輕科研人員穩定的必要支持。
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陳云霽就是在“科學春天”中成長的新一代。他14歲就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讀本科,從此成為科學院的一員,二十多年沒有離開過。
陳云霽在今天的座談會上說,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我國正迎來又一次“科學春天”——以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為目標,就是要領先,就是要成為世界第一,就是要進入無人區,持續領先。
隨著智能科技的飛速發展,人類社會已經開始邁進智能時代。陳云霽所在的計算所,研制了世界第一個深度學習處理器芯片“寒武紀”,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科學》稱之為“顛覆性進展”,并評價陳云霽為國際上智能芯片研究的“先驅”和“公認的領導者之一”。
陳云霽告訴記者,身為80后的他,能夠生在“科學春天”已屬幸運,而更幸運的是,又在自己年輕有干勁之時,遇上這一新的“科學春天”。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北京中小學8月29日起分批錯峰開學 2021年1月30日放寒假-查字典資訊網2020-09-15
北京中小學8月29日起分批錯峰開學 2021年1月30日放寒假-查字典資訊網2020-09-1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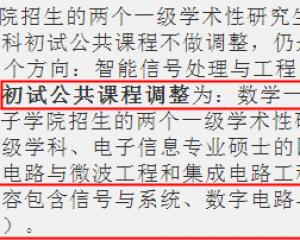
 黑龍江:2020年普通高校本科提前批院校錄取最低分數線-查字典資訊網2020-08-19
黑龍江:2020年普通高校本科提前批院校錄取最低分數線-查字典資訊網2020-08-19 交叉學科將成第14個門類,這些高校早已搶占先機!2020-08-10
交叉學科將成第14個門類,這些高校早已搶占先機!2020-08-1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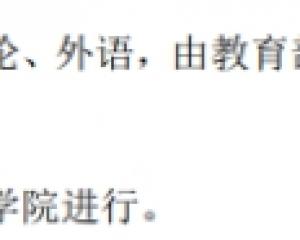 2021考研招生簡章已公布?漢族考生也可享受“少干計劃”的降分優惠?-查字典資訊網2020-08-06
2021考研招生簡章已公布?漢族考生也可享受“少干計劃”的降分優惠?-查字典資訊網2020-08-06